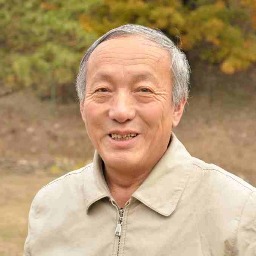第8篇 古朴更胜华丽
承德 杨帆
看红楼梦,你最喜欢的人物是那些珠光宝气的贵妇人?是那些赛过画中人的脂粉包围着的小姐丫鬟?曹雪芹笔下的人物都栩栩如生,我则欣赏刘姥姥和焦大。因为曹雪芹把他们那种最底层劳动人民的古朴刻画得活灵活现,朴实忠厚,正直正义。
庄子曾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古朴,指朴素而有古代的风格。在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思想中,“古”和“雅”是两个联系紧密的概念。《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古雅是《文心雕龙》的理论核心。《文心雕龙》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他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朴素乃是人的底色,根底在于坦荡真诚。朴素的人不做任何的伪饰,不遮不掩地向人坦露自己的真实面目。
金庸武侠小说里我最佩服的人物是《神雕侠侣》中的独孤求败,小说里描写他的剑术进境过程,由追求锋利,到追求重钝,追求古朴,以至后来随手成剑。体现了古朴至上的真谛。
小说里人物有古朴,生活中的人有古朴。活在这个世上,人人都会有朋友。而真正的友情,是一种纯洁高尚、朴素平凡的感情。
“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正的朋友不热烈,不张扬,默默陪伴,让人感觉无十分依赖,却又不能离开。真正的朋友,如茶之清素典雅,会和你缘于品,敬于德,惺惺相惜,无须言语亦会相知相融。
台湾作家林清玄从一位花贩那里得知:几乎是所有的白花都很香,越是颜色艳丽的花越是缺乏芬芳。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人也是一样,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
正如他的文章一样,清新流畅,简单朴素,至真至善,平易近人中却总有着感人的力量。
朴素最美——拥有朴素的美需要拥有丰富灿烂的内心。(摘引了作者物道的句子,在此表示感谢)
与世界相处的最好方式,是朴素。
《菜根谭》有言:“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生而为人,当怀一颗素心,独立于喧嚣尘世。
最简约的生活美学,是朴素。
朴素中自有一番审美的个性。
以上说的是人,下面说的是物。
在绘画中,素色是基础色彩,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
绘画若离开“素”的对比、调和,则难成其美,犹如人缺乏自然的素美之质,即便辅以绚烂的修饰,也只会显得失真、浮夸。
门票是小小的图画,朴素的门票显得本真,自然、纯正。华丽耀眼,素雅怡心。
乌兰布统是古战场,清朝康熙皇帝带兵在这里击败了准格尔噶尔丹的叛兵。康熙二十九年,伊犁河域大清王朝的叛臣噶尔丹暗暗投靠俄罗斯,在西陲作乱,东占喀尔喀藩部,另立王朝与大清分庭抗争。这年夏天,塞外狼烟弥漫,噶尔丹率10万精兵大举东进,在乌兰布通扎下营盘,兵锋直指长城,威逼中原。
康熙亲帅大军征讨。八月一日两军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境内)交战。噶尔丹军将万余骆驼缚蹄卧地,背负木箱,蒙以湿毡,环列为营,名为"驼城"。士兵依托箱垛,发射弓矢。清军以火器为前列,遥攻中坚,摧毁驼城。噶尔丹仅率数千人逃回科布多。

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帝发兵十万,分东、西、中三路出击。五月十三日费扬古统帅之西路清军在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与噶尔丹主力军队遭遇,激战数日,清军猛攻敌军阵后,另遣骑兵进攻侧翼,噶尔丹军阵大乱,清军追击三十余里,歼敌数千。噶尔丹率残部仓惶西逃。次年春,康熙帝亲赴宁夏,命费扬古、马思哈两路出兵,进剿噶尔丹残部。同年三月,噶尔丹在科布多阿察阿穆塔台暴病而亡。
后来虽然雍正和乾隆也都为了征服准噶尔贵族残部而出兵征讨过,但规模小了很多,并且在1756年准噶尔彻底被乾隆皇帝征服。乌兰布通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个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由守转攻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历史上一直骚乱中原几千年的北方游牧部落彻底丧失了南下中原的能力。
我有一枚(自搞收藏以来,只有一枚)珍藏的坝上刚刚有了 有价旅游时,乌兰布统最初始的门票。(见下图)

规格(8 x18 cm),不大不小
门票红色“乌兰布统”不是印章,模仿印章。
蓝色骑马射箭也不是印章,模仿印章。
低劣的纸质,避免乱色,套色印刷,只选用了红黑蓝三种单色印在白纸上。
简单,元素简单,色彩简单,画面简单。原始的石板印刷技术,成本低廉。
我想到了穿着朴素的草原牧人,那艰苦奋斗的林场工人。
透过门票,我仿佛看到了这片古战场几十万人的大战,烟尘滚滚,炮火隆隆,马嘶鸣,飞鸣镝。
设计极简,印刷极简,用纸极简,整体感觉古重、老拙、粗笨,简陋、朴素、实在,内蕴丰富,古意沉沉。我捧着门票,充满敬意。
近些年,乌兰布统出了大大小小多种门票,有的规格很大,例如:

(10x20cm)
纸质好了 多彩印刷,大型票,并带牡丹片邮资。但是,相比之下 ,同样可以收藏,然高低美丑不同,欣赏价值大不一样。"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者为上。
“给艺术的真正力量是融会于伟大情感之中的平凡”。——让我们记住法国画家让·弗·米勒的一句话。
2002年4月13日写于 热河

 编辑:钱宝林
编辑:钱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