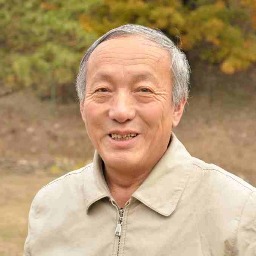全国二十届展“双先”访谈录(16)
先进个人——收藏数量较多的门券收藏家刘洪利
访谈时间:2022年5月30日
访谈人:钱宝林(券研网记者,以下简称记者)
被访谈人:( 吉林省券协常务副会长刘洪利 以下简称刘老师)
(记者):刘老师您好!我们相识在湖北鄂州,邂逅在莲花山下的吉祥宝地,实在是我的一件幸事。久闻大名,其实,我们在2018年的平遥邀请展就应该认识。今天我们坐下来聊聊你这么多年的券事好吗?
(刘老师):首先要感谢门券部授予我全国门券收藏界先进个人的荣誉,这是对自己的鞭策与鼓励,我十分的珍惜。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加倍努力为门券收藏活动做更多的事。很难忘记在湖北鄂州莲花塔下那一声亲切的呼喊,我们有幸结识了钱老师夫妇,兄弟之间的友谊在第二十届全国门券展上开启。是的,我们早就该在平遥全国世界遗产旅游门券邀请展上相识了,那次您也是肩负着宣传报道的重任,真是太忙了。可那一次我也是收获不小,认识了承德券界的强大阵容,长枪短炮烘托了大展的气氛。
(记者):翻看一下券研网,您的第一篇稿子是一则广告:欢迎订阅《东北门券》。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想着要出刊这样一张小报的呢?此前,读张占芝老师的文章,好像您刻蜡纸的时候,办的刊更早一些是吗?
(刘老师):我在1989年10月15日创办了油印小报《旅游与收藏》,1995年9月20日更名为《长春门券》,一共出刊74期。《东北门券》实际上是我办小报的延续,不同的是由张占芝任主编,我是她的助理。油印的小报变成了高规格的铅印报纸,再加上张主编的办报风格,很受全国券友的欢迎。
(记者):从2009年的券研网第一篇发稿,到2019年的第二篇稿子面世,近10年的时间,间隔这么长,您在忙什么?小报还在继续编发吗?
(刘老师):钱部长采访工作很用心,连2009年本人在券研网发的一则广告都查到了,不愧为首席记者,我是由衷的敬佩。那份广告是怎么发的我记不得了,因为那时正是抑郁阶段,精神恍惚。2019年得到了券研网领导的关爱,在张占芝的鼓励之下,我们参与了券研网的活动。由于我俩的底子薄,摆弄电脑很吃力,再加上文化水平低,三年来是边参与边学习,摸索着走到了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这要感谢券研网领导的亲切关怀,网站师友的热情鼓励,张占芝的亲情陪伴。《东北门券》于2010年9月停刊,并不是财力不足办不下去,因为当时的订户很多,资金足够把小报办下去,是因为我审稿疏忽,把不团结的内容编了进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我辜负了主编对我的信任。刚烈性格的主编果断决定停刊,不能当攻击他人的工具。
(记者):到2020年3月,您的《塔林拾珍》专栏在券研网陆续刊发展示,是什么机缘促成的呢?
(刘老师): 我有水塔恐惧症,从小的时候到现在不敢接近水塔。可能外地券友听不懂我说的水塔,它是城市供水用的,伪满时期的建筑,只有长春和沈阳有这种水塔,阴森森的,样子十分的恐怖。有些古塔也有类似的特点,旅游观光时我都拒而远之。我偏偏又特别喜欢塔的门券,前些年一位收藏古塔门券的高手成全了我,接管了他的全部藏品。两人的藏品汇集在一起,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我想把每座塔各编一篇小文,一是形成资料收存,二是借机会显摆一下。在券研网刊发一年后,获得了最佳栏目奖之一。
(记者):截止到目前,《塔林拾趣》已经发了109期,而且像《东北景点的传说》、《黑土地集结号》、《她是怎么来的》等小专栏如雨后新苗,又如火山喷发,让人有点目不暇给。既拾趣,又增识,这里面可以窥见您的藏识和功力,这是多年学习积累养成的吗?
(刘老师):我肚子里的墨水少,一生中也没把一篇长篇小说完整地读下来。喜欢儿童文学之类的读物,所以,自己写的东西从不拖泥带水,让读者尽可能在短时间读完,如果不喜欢省得让人家遭罪。每个人的作品,第一位读者肯定是他自己,连自己都不喜欢的东西干脆就不去写。当然了,由于水平的限制,应该表达的东西没有展示出来,浪费了许多资源。
(记者):荣获先进个人对您的评语是:券友推崇的收藏数量较多的门券收藏家。用“较多”二字是评先组织的精妙之处,不做硬性肯定,是山外有山之意。那么,您收藏的门票到目前统计的准确数目是多少枚?其中东北门券的占比是多少?再一个,收藏这些门券的时间跨度是多长呢?
(刘老师):“较多”一词用得很好,评委给自己留了余地,我也没什么压力。如果用“最多”我就坐立不安了,因为券界高人很多,有的不喜欢张扬。还有些藏家不统计数量,自己收藏了多少也不清楚。每个人计算品种的标准也不同,单单以数量论英雄也不完全合理。平时计算数量是收藏过程中的一个动力,只求数量不顾质量是不完美的。我集门券是全集型,有人称原始的收藏方法,所以平时收获的门券很多,我并不是急于入册,把它们先放在缓冲的盒子里,再用信封分专题和省市存放。闲暇之时再进行入册,然后把整理后的数量加在总数量里。截止到5月30号,记录的总数量为116377枚,还有很多没有统计,如果加在一起应该在12万枚左右。除了总数量外,专题和省份不再单独统计,所以不清楚东北门券的具体数量。实际上我的券龄并不短,和我四十年的工龄差不多,但头二十年是以收藏烟标为主,曾两次用门券藏品换了烟标,现在家藏门券的用时是二十年。
(记者):收藏这么多门券,尽管券友们在收藏门券分类方面各有不同,但很想知道您的门券收藏是如何分类的?要在那么多门券中找到一枚您想看到的藏品,索引能够帮助您很快找到吗?
(刘老师):藏品不多的时候我是按省分类的,省里再按各城市存放。这样的方法很省事,欣赏一省券不用东翻西找。但对提高收藏水平不利,有一种满足感。如果分专题存放,就有了具体的寻找目标,在收藏上容易出成果。现在我把自己喜欢的专题都单独存放,没有列为专题的归入各省。先后的两种存放方法各有利弊,前者欣赏省市券比较过瘾,但找专题券很吃力。后者欣赏某一个专题一目了然,但看省市券感觉缺少很多,我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至今也没什么效果。
(记者):都说我们的门券收藏是“草根收藏”,这个观点我不大认同。其实我发现,门券收藏的大家或是具有一定实力的藏家,也同时具有文人和艺术家的气质和风采,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历史沿革、琴棋书画,可以说无所不及。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刘老师):我们集门券的人,特别是非常上心集门券的人,都有和您一样的体会。我接触过几十项收藏,为什么最终归了门券,就是认为收藏门券最有意义。但在外人眼里并不是这样,他们一般接触不到有成就的门券藏家,更感觉不到门券收藏的魅力。前些年有位省报记者奉命来采访我的烟标收藏,我极力推荐门券收藏内容更丰富,得到的回答是总编没安排,也就是不感兴趣。其实这并不怪别人,证明过去我们只顾埋头收藏,向社会宣传展示的不够,准确点说是真正的门券藏家展示的不够。
(记者):从报道的图片中,经常看到您的“东北门票博物馆”,前几天,有报道说朱龙淮老师亲自前往参观。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博物馆规模及馆藏系列藏品好吗?
(刘老师):其实我早就有自己的收藏馆,但都是家庭式的,券友们交流相对不方便,建立单独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本地和周边的券友有个活动场所。遗憾的是这个馆建的不是时候,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并没有达到我预想的效果。由于不与藏品住在一起,对整理门券也造成一些困难。门票博物馆的规模不大,在我家附近租了个近80平米的房子。设有展示厅和两个收藏室。展柜部分先后展示了五部门券展集,展台部分第一阶段展示了异质门票,第二阶段展示的内容是部分东北磁卡门票。疫情的影响,一年中只举办了两次省内券友交流日。
(记者):其规模和藏品让人羡慕,我想,有机会东北之行,一定要去您的博物馆一睹风采。也希望您的博物馆藏品和人气越来越兴旺。给全国的券友们晒几张东北门券好吗?
(刘老师):好吧。展示几枚给券友老师们看看。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有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刘老师):非常欢迎钱部长及全国的券友来长春做客,券友在一起畅叙友情交流探讨是很惬意的,我期待着。

刘洪利老师2021年10月18日在游览三峡时留影(刘洪利提供)

 编辑:张文革
编辑:张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