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闲鱼上出售的门票集子
赵征宇
“闲不住上闲鱼”,这句戏言成了我与一批特殊藏品相遇的契机。某日浏览闲鱼App时,系统大数据精准推送来一批门票藏品——大部分是四川80年代的老门票,足足上千张、装订成十多本,店主开价2888元。更巧的是,这位店主是成都本地人,专门经营收藏品生意。看到这批带着岁月痕迹的四川老门票,我心头一沉:大概率是某位成都门票藏友离开了,这些凝聚着心血的藏品才流入市场。
成都的门票收藏圈子本就不大,我立刻咨询了几位资深藏友,可他们都表示不认识这位“离开的藏友”。再细品这批门票集子的整理风格——没有明显的协会标记,分类逻辑更贴近个人喜好,我暗自推测:这或许是一位“自娱自乐”的藏家,平日里单打独斗,从未加入过正式的收藏协会,也因此在圈子里少了些“存在感”。

玩收藏几十年,这样“藏品无主”的场面,我见得太多,每一次都让人唏嘘。有些藏友离世后,家人整理他们留下的藏品时,常常边翻边落泪——那些泛黄的门票、规整的册页,每一件都藏着逝者生前的热爱,触景生情的滋味,旁人难懂。可更多时候,这份“珍视”难以传递:有些家人不理解收藏的意义,竟把部分藏品当废纸卖掉。我曾听说,成都一位集邮家去世后,他的儿女将父亲珍藏多年的信封(其中不乏罕见的“双花封”)和旧书资料,一股脑当作废品处理。后来,那些“双花封”幸运地流回了送仙桥旧书市场,被集邮家的生前好友偶然发现、高价买回;可那些承载着更多研究价值的旧书资料,却彻底没了下落,想来大概率已被打成纸浆,永远消失在时光里。
如今的收藏圈,主力军仍是50到80岁的中老年人。他们的儿女大多不懂收藏,也鲜有兴趣接过这份“爱好”。对藏家而言,藏品早已超越了“物品”的意义,有时甚至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生前总觉得“还能再藏几年”,不愿轻易处置;可一旦离世,不懂行的儿女面对满屋藏品,往往手足无措,最后要么低价变卖“败家”,要么干脆当垃圾丢弃。这世间最遗憾的事,莫过于藏家生前珍之重之的宝贝,死后落得如此下场,而这恰恰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结局。
其实很多人都忘了:收藏的最高境界,从不是“占有”,也不只是“研究”,而是“传承”——是文化与热爱的延续。有些藏家早有觉悟,发愿将藏品捐给博物馆,可现实往往泼来冷水:博物馆的目光多聚焦于高档藏品,比如古董、名家字画;像门票、烟标、火花这类“大众藏品”,它们很少愿意接收。毕竟,收纳这些藏品,体制内的工作人员要耗费大量时间整理、清点,无疑会加重工作负担。偶尔,档案馆会接收一部分,但也有严格限制 ——只收与本地相关的资料,外地藏品一概不收。2025年6月 13日,上海照相机收藏家马正康将自己收藏的千件海鸥牌照相器材捐给上海档案馆,外行看了纷纷喝彩,赞其“无私”;可内行人才懂这份“捐赠”背后的心酸与无奈——若能找到真正懂行、愿意接手的“接盘侠”,谁又愿让藏品带着“遗憾”进档案馆呢?

相比之下,日本一些有前瞻性的藏家,做法更值得借鉴。他们往往在 50多岁时,就开始主动为藏品寻找“接班人”,哪怕过程中要“忍痛割爱”,也要为宝贝谋一个好归宿。当然,找“接班人”绝非易事:对方不仅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撑收藏,更要具备专业知识,能读懂藏品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人品要可靠,能真正扛起“传承”的责任。
山西火花收藏家贺守纯老先生,就为藏界树立了一个绝佳典范。80多岁高龄时,他经过慎重考量,将毕生珍藏的火花藏品,托付给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志愿服务协会的魏永轩老师。而魏永轩老师也不负所托,后续在山西多家官方博物馆,策划了多场 “繁华——火柴盒贴上的锦绣中华”火花展览,让原本藏于私人手中的火花,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传递文化的载体,取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这才是收藏传承应有的模样:让热爱延续,让文化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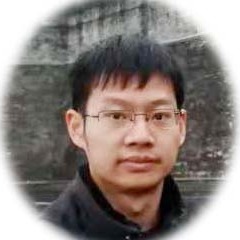 编辑:戴杰
编辑:戴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