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宜宾到自贡,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笔者走了三年多时间。2011年5月17日,我终于走向自贡,第三次造访自号“半百老人”的李克定先生。
八旬老人
记忆刚从“三台寺路17号”切换到汇东李氏新居,一扇似曾见过的防盗门眼前半开。李夫人热情的招呼声裹夹着一阵墨香扑面而来。客厅三面悬挂的书轴依然如故,抢人眼目,不同的是书法作者已戴上助听器,不用夫人耳语传话,便可与我无障碍地对话交流。
刚见面,李老便拿出两张尺许彩照,说是回南京老家过八十生日的“全家福”,并逐一给我介绍哪个是弟、妹,哪个是子、女,同时说起他在老家过生日如何如何快活……。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外貌威严的他,骨子里藏着的童趣和温情。

撰文心得
我俩在书房入座,一边品茶,一边聊天。谈到门券收藏研究,他说:“要把理论研究搞上去,很不容易!需要资金投入,需要‘中券委’特别是整个券界的重视,还要一批有德性的理论研究者,牺牲自我,默默无闻地投入!”说罢他感叹不已:“我办<夕阳红>,感触太多太深,难以坚持,最后只得撒手!”
说到写文章,他指出“券界总的文化程度不高,因此作者要注意阅读对象,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文章太长,没有人看,是一种浪费”。他瞅我一眼,又说:“十堰的李某某到我家来过,他的文章可读,就是太长……”
听到这里,我差点笑出声来,心想这个老学究还是这么精怪,帮助人不直说,爱搞“声东击西”,他哪里是说李某?分明是在点化我。
券坛论道
说到“旅游门券”的定位,李老滔滔不绝:“我一直在考虑,门券收藏比较活跃,品味亦高,但就是不能和其它藏项相比,门券的品牌总是打不出去!怎么去把它的位置改换一下?有些人也在考虑,不搞门券收藏,搞 ‘旅游文化’。这样定位,范围就宽了,牌子很大,实际搞的又窄。即便把旅游纪念品、导游图、简介、书报等等都包揽进去,说是‘旅游文化’还是不够。真正的旅游文化要在深层次上和旅游产业相结合,牌子才能立起来。不然旅游界不当成一回事。我理解,打旅游牌子是想靠旅游行业摆脱门券收藏的尴尬局面,但总的是难。要找到旅游切入点并非易事,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我就丢了!”

他说这番话,语气委婉客观,不象写文章那样措辞激烈。或许他认为我是个“旅游门券”论者,又出于待客的礼节?我们无从辩论,倒不是因为亦师亦友的情份。因为在“门券”与“门票”的争论上我们都赞同“两论并存”,在门票大于旅游门票的内涵概念上没有分歧;在寻求门券收藏的推动力上有着互通的出发点。
如果硬要找出不同的话,或许是我仍然定格在“旅游”与“文化”这个切入点上,轻淡了“收藏”,并坚持在切入点上努力寻求突破的机会。我至今认为,券界上下从旅游切入的成功案例不少,值得我们去梳理和总结。券界太需要广纳贤才,今后,只要有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进入券界,我们都要千方百计留住!一旦机遇来临,券界就有可能重视全国第十届展时的辉煌!
往事留痕
提到届展评审,我们追忆重庆往事。他认为江西那部红色展集落选,主要是评委年轻,资深者又跑马观花,马虎了事。由此看出评奖有不公正的因素,很难说公平,今后应当引以为戒。李老似乎想举例说明,刚说到“我欣赏那部石头集”时,突然象一休哥那样拍叩脑门:“唉,忘了题名……”
我说:“叫《石韵》”。
他点点头,仍然拍着头顶:“想不起作者了!”
我又接上一句:“丁鸣”
这时李老对《石韵》赞不绝口:“这个选题颇费心机,很多根本不相连的东西,都联上了。他把石头钻透了!这部展集无政治价值,但艺术造诣很深!可惜没得到最佳奖。”
激情依旧
我们的话题沿着集券主线驰骋跳跃,自然地落到四川省第三届展览上。他直率地讲:“我只谈两点重要,选好展览场地,观众多,效果好。再是宣传工作,报纸、电视台、广播站都要上,声势舆论很重要!”

说到展品征集,他顺手拿出一部题为《红色》的三框券集,说是参展作品。我哪里肯放过?便逐页细看,感到标题简洁,时代感强,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看罢我的《券友赋》展集设计小样,表示赞许:思路新,表现形式独特,连说“很多人都想不到”!
提到券界二年展,我说今年是疑云密布,或许期待来年了。他接过话头:“明年如果举办全国展,我参展的专题名称都想好了——《上下五千年》”
听了此话,我脱口而出:“天津的孟昭怀也有部《上下五千年》,据说贴片过千张!”
李老笑了:“我不搞那么细,划粗线条。”随后又加上一句:“碰车也无妨!各搞各的,可以比一比!”
我不禁抬起头来,仔细地欣赏他那张三分威仪七分认真的脸,按捺不住内心的惊喜:“好个半百老人!这只‘老虎’终于要出山了!”
情洒券界
或许是多灾多难的磨砺,让这个八旬老人养成从不午眠的习惯,在6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毫无倦意,对门券收藏一往情深。他非常热情地说:“现在条件成熟了,请‘中券委’发号召,组织一个编撰班子,出一部《门券收藏词典》”接着又露出很遗憾的表情:“我曾经启动过,没有成功。有刘永禄、冯达材参与,”他想了想又说:“还有哈尔滨那个王(庆堂)……郑州那个……记不清了。”他又拍着自己的头顶——第一次看见这个“老一休”的动作,我真的心里发笑,但是再次听见这个长者拍叩脑门的声响,我的心灵却被强烈地震憾了!
克定老矣,血液依然滚烫!
他正在归纳藏展见识,准备第二册《散论》式文集付梓。
他还在选门券、上贴片、编“专题”,准备在自贡办一次高品味的门券收藏展览,希望在物欲横流的世界,给后人留下一处鸟语花香。

临别,李老在近作《书散集》扉页为我题赠,当我掀动快门的瞬间,突然想一声呼喊:“永不沉没的小舟”!
【编辑:王建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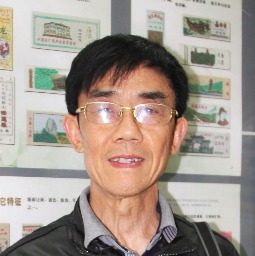
 编辑:王建池
编辑:王建池













